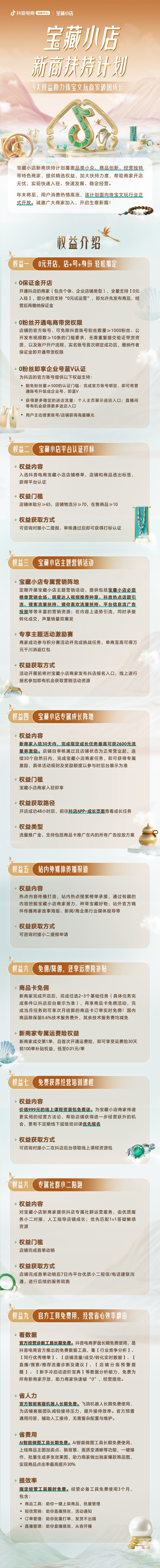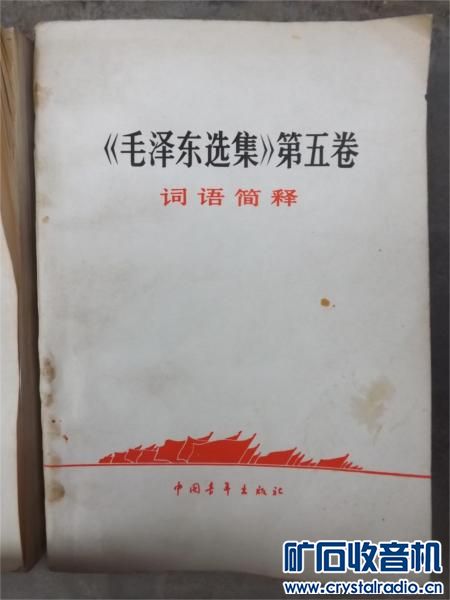
一些文革书籍一怀念那个年代
潘小松
优雅海扇蛤,扇形的贝壳纹路形似从侧面看一本翻开的书,一页一页似乎都在流动,而浅黄色是旧书特有的岁月痕迹。
去年“光棍购物节”往回数四天,我到位于北京花家地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看展览,无意中碰上了第二届全球艺术家手制书展。展品的花样不少,但都有一个突出的焦点——打破传统印刷书籍的概念,把书的“外延”开发到极致。
我这才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前卫。1998年至2004年间,我曾在北京潘家园居住了几年。由于当时家里的阳台色彩单调,我就用不成套的《苏联大百科》以及60卷本的列宁全集砌阳台。
那个时候旧书廉价,我拿《希腊画册》垫君子兰花盆。遇上喜欢的1880年前后出版的毛边英文版《柏拉图文集》,我会剪掉缎子被面,用它来糊破书的封面。这种糊封面是我手工制作书籍的雏形。
发展下去,就是找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带有浓厚时代意识形态特征的笔记本,或者民国旧账本,往里抄写一些东西。这是我手制书籍的第二个阶段。
我曾在烟袋斜街一家卖牛皮制品的店里发现多种适合书籍封面的笔记本。它们的样子很像艾柯《玫瑰的名字》里教堂里的圣书。于是,我觉得不妨把笔记本的瓤子去掉,剪裁一下,就可以当我的旧书的封面。我昔日搜集了许多老版本《圣经》和双语词典,它们的年龄总在百岁以上,“衣服”难免破败。想及此,我便试验了一下旧书“换衣”,结果发现它们“容光焕发”。这又是一个阶段。
许多旧书文本阅读价值和参考价值在个人手里无法体现,而它们当年被生产时所用的材料却很好。在北京城的洋咖啡还算奢侈品的时候,出版于1870年前后的《英国皇家农业年鉴》皮装本却很廉价,廉价到按废纸论斤算价格。有些咖啡馆就拿这些东西当装饰品,一杯咖啡的代价能换10来本这样的书籍。
假如把这些书籍的衬纸取下来,就是很好的手工藏书票的制作材料。旧法文小说的余纸空白叶和插图都是制作藏书票最佳原材料。因为,旧小说的插图大抵为木版画甚至铜版画。空白页泛黄,很有旧票的韵味。这也可称为另一种形式的手工制书。
文本发展到今天一如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然“无非文本”,没有什么不是艺术了。于是人们往空白本子里盖戳、添加文本,把旧信旧邮票都弄成文本,甚至把带有印花的碎布贴到本子上……
我看完展览后发现自己的影集盒子里有许多文本的边角料,比如版权页、扉页、书脊的旧残存,于是动念买一本在烟袋斜街新发现的手工痕迹更重的厚皮本子,把这些“残纸破页”贴上去。我更把20年前乔伊斯研讨会的邀请函夹贴进去,那里面有爱尔兰的信息,有《尤利西斯》的译者萧乾、文洁若的信息。我把旧书里夹着的“明星电影院”的电影票贴上去,把镇江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的门票贴上去。这个手工书里还有剪报,那是我不曾结集的散乱文字,有些都被遗忘许久了。
我自己今年行走的地方不少,也买到许多纸质文本,比如武汉大学手绘地图、诗人汪静之的纪念册,以及抗战70年纪念勋章的说明书等。然而,我觉得这些都不如发现手制书新路径来得喜悦。
这个时代,文本的革命性变化注定影响深远。人们举办手制书展览是对一个渐行渐远时代的怀恋,略带挽留的情绪,同时也是对文本概念的困惑。新时代文本因为缺少时间考验而未被证明属于经典,加以文本的泛滥,人们于是觉得不如直“书”胸臆,把原生态的文本留给世人。
手制书是手工热的余脉。对我等喜欢旧书的人来说,手工的主要目的是“修旧如旧”,是对机器整齐划一的“反动”。而从某个收藏角度来说,手工因为制品量小,得以成令人垂青的“藏品”。